【雅士】 白先勇 四百年青春之梦

任何一种文化的衰萎,我都会很心痛。如果昆曲从我们这一代的手上消逝,我们就是历史罪人;这和我们把宋朝的瓷器摔了,把殷商的青铜器砸了没有任何区别。于是,我选择了推行昆曲的复兴——我想,只要去做,就来得及。
——白先勇
当今,寂寞已久的昆曲艺术以其仍然神秘高雅的姿态,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数百年前,听昆曲,唱昆曲,一度是国人最贵族、时尚的生活方式;如今,《牡丹亭》与《玉簪记》的笛声,穿越600年的时光悠扬再响,似乎往昔的繁荣近在眼前,令人触目可及。
“很多伟大的民族,都有其高雅精致的表演艺术,深刻地表现那个民族的精神和心声。希腊人有悲剧,意大利人有歌剧,俄国人有芭蕾,英国人有莎士比亚戏剧……这些雅乐,往往是其民族骄傲与自信的源泉。那么,中国人的雅乐又是什么?毫无疑问,是昆曲。”白先勇先生如是说,岁月在这位72岁的老人身上竟未留下太多痕迹。提起昆曲,白先勇先生依然抑制不住地兴奋与向往,仿佛青春的不止是昆曲,还有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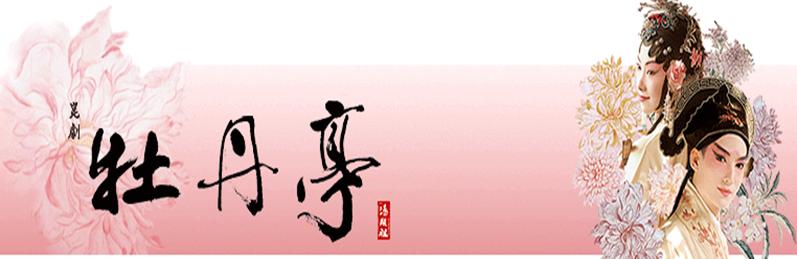
穆赫然:此次来京,您除带来新版《玉簪记》,更重要的是启动“北京大学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如此浩大工程,是您推广昆曲最初即有的心愿吗?这个心愿又是如何产生的?
白先勇:这个昆曲传承计划并非灵光一动、即兴而出的念头。它是我构思多年的周密详尽的一个大计划。几百年前,国人万人空巷地看昆曲,那是一种如火如荼的狂热场面;而几百年后的今人,却与昆曲隔阂。几年前,我倒苏州大学推广昆曲,发现即使昆曲发源地,居然也鲜有听过昆曲、了解昆曲者。这可是在苏州啊!由此可以推想全国其他地方的昆曲状况又将如何。从那时开始,我就产生了开展昆曲传承计划的想法。
昆曲,不仅只是昆曲,也不仅只是做戏。昆曲,号称百戏之母,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精髓、最精致也是最精确的表演艺术,堪称极矣至矣尽矣。我想借推广昆曲的风势,同时大力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美。但与所有艺术一样,昆曲也讲究“需求”。有需才有求,尽管台上的昆曲唱得甚好,但台下仅有数名观众,昆曲注定只能到博物馆养老;反之,如果形成热爱昆曲艺术的社会氛围,有无数观众拥趸支持昆曲的话,昆曲便就恢复了繁荣的局面。由于有需求,便会有更多演员投身昆曲艺术,主动寻师求教,热情学习……如此,昆曲的发展怎会不好?如果街头巷尾,人人都能哼唱几句昆曲,人人都能谈论昆曲折子时,高雅的昆曲本便已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成为日常之美。那时,昆曲的书籍、讲座便会增多,甚至出现专门的昆曲剧院、昆曲电视台……这并非不可能的。这就是我的“昆曲传承计划”的最终目的。
穆赫然:请向我刊读者详细地透露一些“北京大学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的具体内容。
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很大,也很漫长,包括在北京大学开设经典昆曲鉴赏课,看展昆曲艺术的学术研究,出版昆曲大师的相关传记,举办昆曲讲座、研讨会,举办昆曲经典剧目及大师汇演,建设昆曲艺术数字平台和昆曲影像数据库,培养新一代昆曲艺术人才,等等,内容极其丰富。但具体步骤则分三步:第一步是“亲近昆曲”也叫“了解昆曲”,第二步是“学习昆曲”,第三步是“研究昆曲”。此计划的第一阶段持续5年。目前当务之急是“昆曲走进校园”,惟有进校园,昆曲才有走向世界的可能。亲近和了解昆曲是第一步,也是很难的一部。人们都说,年轻人不看昆曲,甚至连昆曲具体是什么都无从而知,即使知道,也是非常“扼要”地知道,如其只知昆曲很高雅,很高端,其他的便无所知之。所以,这一步是“从无到有”的过程。昆曲要传承,要发展,一方面需有好的老师,好的演员,更重要的是有好的观众。因为,艺术是互动的,美是相对的。如果没有好的观众营造痴迷昆曲的社会大环境,纵然昆曲师傅教得再好,仅靠几个学得再好哦新演员,也无济于事。
培养昆曲的好观众,应从大学生入手。其实,无论大陆还是港台地区,新一代大学生对传承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普遍有种隔阂与疏离。并非他们真的不喜欢,而是他们所能接触的范围太窄。我们的学校没有昆曲赏析,更遑论开设相关的课程,没有相应的教育环境和计划,学生即使想喜欢昆曲也无从喜欢起呀!并非人都有杜丽娘那般的奇遇,无需从见到柳梦梅便能爱上他。所谓“昆曲传承计划”,就是杜丽娘邂逅柳梦梅的过程,使大学生们能够接触真正的昆曲,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美学中最精致的呈现手法,然后再论喜欢不喜欢。惟其了解,才能懂得。

青春版《牡丹亭》巡演5年多,到过大陆和港台地区的数十所著名大学,每场演出,气氛热烈,常常爆满;有座者坐着看,没坐者站着看;甚至常常来看,次次来看,无数大学生由此痴迷上昆曲。由此说明,昆曲并非单纯古老的表演艺术,它还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不要指责当下的大学生趋于时尚,忘记传统;而是他们生活的现代社会使之无法接触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旦接触,他们便会喜爱。因为时尚和传统并不相互抵触,传统是传承不断的时尚,时尚是累积未来的传统,昆曲可令数百年前的文人雅士痴迷,今天它同样能使大学生们欣赏与折服,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昆曲是一种独特的美学,只要是美,就是人们天性中的碌碌追求,其百年不变,千年不变。据我了解,即使从未看过昆曲的大学生,很多看了以后都觉得,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原来有这么美的东西。我认为,这是一种了不得的教育。
穆赫然:对于初次接触昆曲的观众而言,是否会有听不懂的现象?
白先勇:我最怕观众听不懂,听不明,坐不住,认为曲高和寡……与京剧强调的忠孝礼义不同,昆曲的主题更多的是爱情,无论爱情史诗《牡丹亭》还是爱情小品《玉簪记》,都极易与观众共鸣,只要你做的住,仔细听,很容易隋剧情的喜怒哀乐而被感动。据我所知,看过我的《牡丹亭》和《玉簪记》的观众,无论大学生还是老人家,不仅没有打瞌睡的且几乎始终兴奋。没听过昆曲的会因此喜欢昆曲,听过昆曲的会更喜欢昆曲。欣赏昆曲的唯一敲门便是用心听,只要认真倾听,便能发现其中无穷之美。
穆赫然:您一直强调复兴昆曲中,古典美学与现代生活结合的“度”。您认为这种结合是否会有损传统?毕竟现代社会和古代差异很大。
白先勇:总之,昆曲古典美学与现代生活美学的结合,是必然趋势。我认为,要把握一个大的原则,即尊敬古典,但不因循古典;加入现代,但不滥用现代。所以,在古典与现代的接点,我们非常地小心。
我认为,昆曲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就是因为文化的关系,如果不对之加以有效传承的话,昆曲便可能衰萎。昆曲与观众日益疏远,使我感到危机,便想是否进行尝试,以期引起人们新的热情,此即我推广昆曲的目的。我希望更多的人一起来做此事。因为,昆曲的复兴不能只靠少数者的努力。很多人说,昆曲这个老剧种,会像自然物种一样将慢慢消亡,如此才顺应规律。我不同意如此说噶,为何希腊悲剧至今没有消亡。希腊悲剧历史数几千年,昆曲才600年;而希腊悲剧至今在演,是因其本身站得住脚,艺术价值极高;同样,昆曲也是因此而存活至今。我对昆曲的美学颇有信心,对其承载的传统文化有信心;我之所以主动推广昆曲,自以为“昆曲义工”,是因为我真的喜爱昆曲。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果然正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便将昆曲收入其中。可以说,我比他们行动得还早。

穆赫然:“从青春版《牡丹亭》和新版《玉簪记》中,观众看到您对各类感官之美无止境的要求,如李祥霆先生演奏的唐琴,王童先生设计的服装,舞台上名家字画的背景……但又专家诟病,此乃形式大于内容,真正的昆曲应将重点放在演员的表演方面。您是为了在年轻人中推广昆曲而做出各种时尚设计呢,还是认为这种设计是昆曲发展必不可少的部分?
白先勇:昆曲既然是曲,延长当是首位。昆曲演员均行三拜九叩的大礼,拜了师傅且一直在学习,尤其演唱半点马虎不得。但我始终认为,若想推广和宣传昆曲,除演员要唱的好,服装、舞美也应尽善尽美。因此,昆曲本身就是唯美的艺术,演员唱得再好,若无细节搭配,也是枉然。所以,我的标准是怎么好久怎么做,仅服装便设计了近200套,每套都是苏州手工刺绣,每朵花都有层次,一朵梅花有三四种颜色,红的,稍淡点儿的粉红,以上舞台,那花是立体的,突出来,而非平的……总之,能做多精就做多精,能做多美就做多美,一定要求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不能在任何细节有所疏忽。
穆赫然:除针对大学生的“昆曲传承计划“外,您认为社会精英能否成为昆曲复兴的组成?
白先勇:大学生是未来的观众,将来的昆曲环境则需要他们的营造,他们也是未来的精英。同样,昆曲也需当今精英的支持,观看昆曲者并非都是学生,各行各业有众多昆曲爱好者,都是当下支持昆曲发展的中坚。昆曲的复兴,需要更多更广范的支持,无论数千人的昆曲演出,还是十数人的私人雅集,本质都是昆曲现代发展的体现,人们以各种形式弘扬昆曲,现阶段都是积极的,无论真心喜爱还是向往风雅,都是一种积极的力量。

穆赫然:除了“昆曲传承计划“外,对于昆曲发展您还有何愿望或期待?
白先勇:条件允许的话,我希望能有一家篆书昆曲的戏院。如此,一来可不必跑来跑去地到处巡演,而来也可更好地服务于昆曲。由于昆曲的特殊性,戏院最好分两层,800—1000席位,景深要大,适合梦幻的背投,且音响效果一定要好,专门服务于昆曲。西方歌剧、芭蕾等高雅艺术,均有专门的演出场地。我相信,随着“昆曲传承计划“的推行,年轻的观众一旦培养出来,昆曲便将真正流行,其地位决不在歌剧或芭蕾之下。
另外,我希望全社会珍惜昆曲演员,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机会,在昆曲复兴中,使之将昆曲艺术弘扬到底。任何一种文化的衰萎,我都会心痛。如果昆曲从我们这代消逝,我们就是历史罪人,这与把宋朝的瓷器摔了,把殷商的青铜器砸了,没有任何区别。
摘自:穆赫然《中外文化交流》 2010年第三期
下一篇:【雅士】蒋勋:美,回归人的原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