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一部有关文学的荒诞小说――读木心《文学回忆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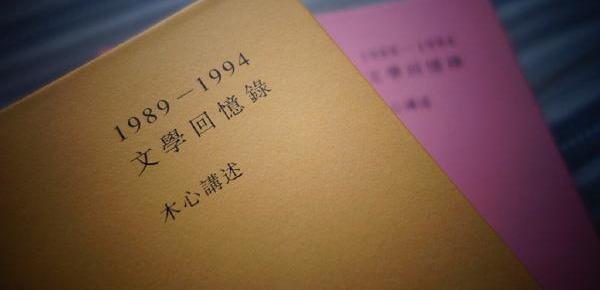
【编辑推荐】
2012年底,木心逝世一周年之际,陈丹青公开了十八年前的木心讲义,并将他在纽约听课时的五大本笔记录入电脑,交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逾千页的《文学回忆录》。这部书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文学史,而是一位历经风霜、睿智达观的老人对于文学的见识,甚至可以说,这是木心有关文学的一部荒诞小说,有些出乎大家对文学常识的意料,有些直接将大家对文学的偏见打破。
每堂课的讲义,木心手写近2万字。陈丹青回忆道,木心老师做学问的态度十二分老实,即便讲到土耳其、波斯或印度作家,他也将不同作者姓名的拼写法端端正正写出来,讲到关汉卿、汤显祖,则将其生卒年月写清楚。令学生们惊异的是,木心并未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几乎全凭自己的记忆力讲述各国文学史。
陈丹青说:“我所迷恋的是木心以及他这代人的语言方式,通透、温厚、泼辣,大道理讲得具体生动,充满细节和比喻,一针见血,丝毫没有空话套话,没有学术腔。”木心正式的写作,虽比张爱玲、周作人、沈从文等人晚很多,却更有“五四”文风,如凤凰浴火般,带着古典的含蓄悠远之美,用现代白话,娓娓道来;他历经坎坷,但不惊不怒,超脱于表象之外,把点滴琐事,用诗歌般的语言,轻叹慢说,些微感悟,字字珠玑,干净、熨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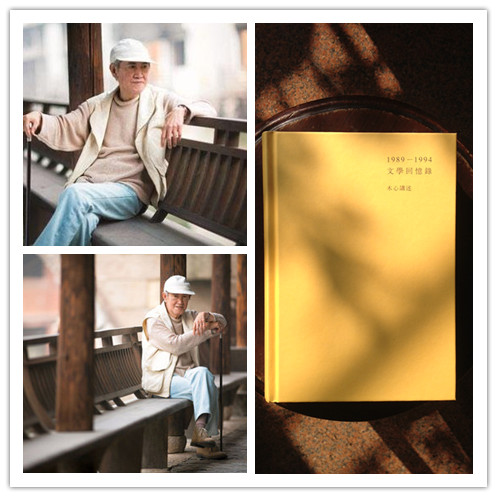
【作者简介】
木心,1927年生,原籍浙江桐乡乌镇人。海外华人文化界传奇式大师,画家,作家。原名仰中,号牧心,笔名木心。1946年,师从林风眠,入“杭州国立艺专”探讨中西绘画。曾任杭州绘画研究社社长,上海市工艺美术协会秘书长,《美化生活》期刊主编,交通大学美学理论教授。
1971年,他在文革期间入狱。狱中,木心用写“坦白书”的纸笔写出了洋洋洒洒65万言的《The Prison Notes》(《狱中笔记》)。1982年定居纽约,从事美术及文学创作。从1984年起,台湾洪范、圆神、远流等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木心作品,包括:散文集《琼美卡随想录》、《散文一集》、《即兴判断》、《素履之往》、《马拉格计画》、《鱼丽之宴》、《同情中断录》;诗集《西班牙三棵树》、《巴珑》、《我纷纷的情欲》、《会吾中》;小说集《温莎墓园日记》等。他的部分散文与小说被翻译成英语,成为美国大学文学史课程范本读物,并作为唯一的中国作家,与福克纳、海明威作品编在同一教材中。他的画作被大英博物馆收藏,这也是20世纪的中国画家中第一位有作品被该馆收藏的。2006年,木心归国定居乌镇,2011年12月21日,病逝于此。

【陈丹青回忆木心讲课始末】
23年前,1989年元月,木心先生在纽约为我们开讲世界文学史。初起的设想,一年讲完,结果整整讲了五年。后期某课,木心笑说:这是一场“文学的远征”。
“文学远征”始末
1982年秋,我在纽约认识了木心,第二年即与他密集过往,剧谈痛聊:文学课里的许多意思,他那时就频频说起。我原本无学,直听得不知如何是好。我不愿独享着这份奇缘,未久,便陆续带着我所认识的艺术家,走去见木心——上世纪八十年代,纽约地面的大陆同行极有限,各人的茫然寂寞,自不待说——当然,很快,众皆惊异,不知如何是好了。逢年过节,或借个什么由头,我们通宵达旦听他聊,或三五人,或七八人,窗外晨光熹微,座中有昏沉睡去的,有勉力强撑的,唯年事最高的木心,精神矍铄。
1989年元月15日,众人假四川画家高小华家聚会,算是课程的启动。木心,浅色西装,笑盈盈坐在靠墙的沙发,那年他六十二岁,鬓发尚未斑白,显得很年轻——讲课的方式商定如下:地点,每位听课人轮流提供自家客厅;时间,寒暑期各人忙,春秋上课;课时,每次讲四小时,每课间隔两周,若因事告假者达三五人,即延后、改期,一二人缺席,照常上课。
开课后,渐渐发现或一专题,一下午讲不完。单是《圣经》就去两个月,共讲四课。上古中古文学史讲毕,已逾一年,越近现代,则内容越多。原计划讲到十九世纪收束,应我们叫唤,木心遂添讲二十世纪流派纷繁的文学,其中,仅《存在主义》便讲了五课。
木心讲课没有腔调。他语速平缓,从不高声说话,说及要紧的意思,字字用了略微加重的语气,如宣读早经写就的文句。录入笔记的这半年,本能地,我在纸页间听到他低哑苍老的嗓音。不止十次,我记得,他在某句话戛然停顿,凝着老人的表情,好几秒钟,呆呆看着我们。这时,我知道,他动了感情,克制着,等自己平息。
“结业”派对,是李校长安排在女钢琴家孙韵寓所。应木心所嘱,我们穿了正装,分别与他合影,孙韵母女联袂弹奏了莫扎特第23号钢琴协奏曲。阿城特意从洛杉矶自费赶来,扛了专业的机器,全程录像。席间,众人先后感言,说些什么,此刻全忘了,只记得黄秋虹才刚开口,泪流满面。木心,如五年前宣布开课时那样,矜矜浅笑,像个远房老亲戚,安静地坐着,那年他六十七岁了。就我所知,那也是他与全体听课生最后一次聚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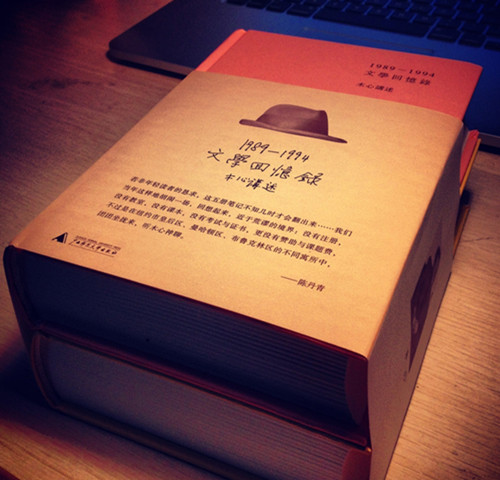
【《文学回忆录》精选】
诗经、楚辞
如果中国有宏伟的史诗,好到可比希腊史诗,但不能有中国的三百零五首古代抒情诗。怎么选择呢?我宁可要那三百零五首《诗经》抒情诗。任何各国古典抒情诗都不及《诗经》,可惜外文无法翻译。
《离骚》,能和西方交响乐——瓦格纳、勃拉姆斯、西贝柳斯、法朗克——媲美。《楚辞》,起于屈原,绝于屈原。宋玉华美。枚乘,雄辩滔滔。都不能及于屈原。唐诗是琳琅满目的文字,屈原全篇是一种心情的起伏,充满辞藻,却总在起伏流动,一种飞翔的感觉。
魏晋文学
中国的文学,是月亮的文学,李白、东坡、辛弃疾、陆游的所谓豪放,都是做出来的,是外露的架子,嵇康的阳刚是内在的、天生的。
汉赋,华丽的体裁,现在没用了。豪放如唐诗,现在也用不上了。凄清委婉的宋词,太伤情,小家气的,现在也不必了。要从中国古典文学汲取营养,借力借光,我认为尚有三个方面:诸子经典的诡辩和雄辩,今天可用。史家述事的笔力和气量,今天可用。诗经、乐府、陶诗的遣词造句,今天可用!
中世纪欧洲文学
好比一瓶酒。希腊是酿酒者,罗马是酿酒者,酒瓶盖是盖好的。故中世纪是酒窖的黑暗,千余年后开瓶,酒味醇厚。中国文化的酒瓶盖,到了唐朝就掉落了,酒气到明清散光。“五四”再把酒倒光,掺进西方的白水,加酒精。
《神曲》涵盖甚大,中世纪哲学、神学、军事、伦理。以现代观点看,《神曲》是立体的《离骚》,《离骚》是平面的《神曲》。《神曲》是一场噩梦,是架空的,是但丁的伟大的徒劳。
中国古典戏曲和文学
中国剧作家的创作观念是伦理的,寓教于戏。有了这种观念……儿女情长,长到结婚为止;英雄气短,短到大团圆……不过是忠孝仁义,在人伦关系上转圈圈。
中国人的民族性,很善说故事。小时候家中佣人、长短工,都会讲故事,看去很笨,讲起来,完全沉浸在故事里,滔滔不绝。中国哲学家也比西方哲学家更喜以形象说理,放进很多神话、传说、寓言,甚至笑话——这或许就是先秦诸子夹着早期的袖珍小说……那时的谋士、策士,进谏皇帝,也要会讲故事,否则要杀头。
在我看来,古代小说是叙事性的散文,严格说来不能算小说。直到唐代,真正的小说上场,即所谓“传奇”。唐人传奇精美、奇妙、纯正,技巧一下子就达到极高的程度,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等西方短篇小说家若能读中文,一定吃醋。
日本古典文学
抱着原谅的心情去看这些诗,很轻,很薄,半透明,纸的木的竹的。日本味。非唐非宋,也非近代中国的白话诗。平静,恬淡。
我是日本文艺的知音,知音,但不知心——他们没有多大的心。日本对中国文化是一种误解。但这一误解,误解出自己的风格,误解得好。
十七、十八、十九世纪英国、欧洲、美国文学
歌德有格言:回到内心。陶潜的《归去来兮辞》,就是回到内心。
奥斯汀太嗦,狄更斯太通俗,但我就是喜欢这两位作家。艺术上前人和后人的关系,是艺术上的天伦关系:前人哺育后人,后人报答前人,成天伦之乐。
哈代的行文非常迟缓,我读时,像中了魔法一样。他行文的本领,音乐家应该羡慕:如此长,温和。读时,心就静下来,慢下来。他写苔丝早起,乡村的种种印象描写,无深意,无目的。就是这种行文。
知识学问是伪装的,品性伪装不了的。三年讲下来,不是解决知识的贫困,而是品性的贫困。没有品性上的丰满,知识就是伪装。
“历史是更伟大的圣经。”这话也是卡莱尔说的。说得好!我们讲文学史,是在讲文学的圣经。我们学文学,就是文学的神学。
中国从未被西方了解过。太可怜,太神秘。中国,不可能被西方汉学家来了解,还得我们自己来——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告诉他们不懂的事……西方最缺的就是中国的东西:含蓄,以弱制胜。东方西方要是真的相通,文明才开始。可是要唤醒东方、中国,非得西方来理解。
要去评价一个伟大的人物,你自己是怎样一个人物?这是致命的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粗糙是极高层次的美,真是望“粗”莫及,望“粗”兴叹。如汉家陵阙的石兽,如果打磨得光滑细洁,就一点也不好看了。尊重这粗糙,可以避免自己文笔光滑的庸俗。
文学的最高意义和最低意义,都是人想了解自己。这仅仅是人的癖好,不是什么崇高的事,是人的自觉、自识、自评。
最近又读一遍《复活》,实在写得好。笔力很重,转弯抹角的大结构,非常讲究,有点像魏碑。
二十世纪文学
世界上的书可分两大类,一类宜深读,一类宜浅读。宜浅读的书如果深读,那就已给他陷住了,控制了。尼采的书宜深读,你浅读,骄傲,自大狂,深读,读出一个自己来……《道德经》若浅读,就会讲谋略,老奸巨猾,深读,会炼成思想上的内家功夫。《离骚》若深读,就爱国、殉情、殉国,浅读,则唯美,好得很。《韩非子》,也易浅读。
谈主义,是一种现代病。试看古人,从雅典到文艺复兴,都不标榜主义。因为主义总是一种偏见,甚至是强词夺理,终归是自我扩张,排斥异己。
“那个才气超过你十倍的人,你要知道,他的功力超过你一百倍。”刚才来讲课路上,我想到这么一句。自己耕耘,自己收获,自己培养自己,自己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诺贝尔奖,好像是个世界性的中状元。
文化好比一瓶酒。希腊是酿酒者,罗马是酿酒者,酒瓶盖是盖好的。故中世纪是酒窖的黑暗,千余年后开瓶,酒味醇厚。中国文化的酒瓶盖,到了唐朝就掉落了,酒气到明清散光。“五四”再把酒倒光,掺进西方的白水,加酒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