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生活】志在高山 云生足下---登高意象的诗意领悟
人们说起登高,首先想到重阳,
然而登高并非重阳节的专利。
中国人自古崇尚登高望远,
古诗词里流传下无数文人骚客登临的诗句。
比如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雄武之情洋溢于胸,这是一代帝王应有的风度。
登高处,可以是自然的山川,
也可以是人造的楼台。
凡人视野有限,
所以谁都想看一看那楼外楼、山外山。
唯一和今人大概不同的是,
古人登高,不是为了观景,
也不是为了某个节日,
当然更不是为了旅游,
只是为了一展胸襟。

沐斋作品《陟岵》
文人登高,如同好汉饮酒,
喜欢自然是喜欢的,
但更重要的是,
他们借助这种方式获得一种不可言传的
类似于“天人合一”的抒发和共鸣。
儒家的登高,是为接近心中至高无上的“仁”;
道家的登高,是为寻求成仙得道的“仙”;
皇帝祭祀封禅,要登天下五岳;
沙门礼佛修行,要临四大道场。
在古人心目中,
高山是最与苍天相近的地方。

沐斋作品《卷耳》
这是一首真正旷绝古今的绝唱: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初唐诗人陈子昂为何登台而哭?
他不是像齐景公那样畏惧未来的死亡,
而是用登高之泣表达了与阮籍类似的情感:
“可悲啊!古今渺渺,天地茫茫,
而人不过如沧海一粟!”
这里面有陈子昂的怀抱。
而陈子昂的的确确是自发地哭,
为自己而哭,
一个人在天地里哭。
大抵汉魏南北朝人多有此意,
陶潜的“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
曹植的“高_多悲风,朝日照北林”,
态度如出一辙。
初唐以降,诗人所作登高诗文,
不再有天地之悲,人生之泣,
李白那样天马行空般的豪放俊逸,
和宋人那样淡云疏月式的清愁
代替了前代深沉的古韵悲思。
登高壮观天地间,
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
白波九道流雪山。
李白的这两句诗,
可谓一笔写尽登高望远的超拔情志。
然而古往今来,
李白、王之涣们的登高诗
所表达的积极情绪并非主流,
诗人们大多在自己登高所赋的诗句里
倾泻了无尽的悲悯、怅惘和迷失,
这种消极意味占据了古今大多数的诗篇
——这是怀抱不能伸张的代价。
由悲到愁,
消极的程度表面看似乎减弱了不少,
实则不然,
因为这份情绪早已深入骨髓,无法自拔,
成为国人“集体无意识”之一部分。
来看唐人咏天下“三大名楼”的诗歌。
先是“初唐四杰”的王勃,
他赴宴滕王阁,
流光溢彩、觥筹交错的热烈氛围下,
挥笔却是阵阵清寒: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王勃《滕王阁诗》
接着来看与李白同时的崔颢,
他登临黄鹤楼的题诗号称唐人七律之绝唱,
连诗仙都自叹弗如。
但笼罩在绝妙诗句间的况味,
仍摆不脱一个“愁”: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崔颢《黄鹤楼》
至于一贯苦吟的老杜,
登上岳阳楼之后所诵的诗篇,
何止是苦,
又岂止是愁: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杜甫《登岳阳楼》
少陵老矣,
岳阳楼上的老者老泪纵横,
不复有当年《望岳》时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的豪迈气概。
那时候,想登高,
未能登,
壮思却比山还要高;
现如今,
登上个楼阁即涕泪交流,
这便是岁月,
这就叫人生。

杜甫已知命——
不光知自己的命,
也知国家的运命,
运命便是人世间这桑田沧海,
天道正在其中。
或者用辛弃疾的话来说,
未登高时“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
待上得高处时,已老态龙钟,
只得“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杜甫的《登高》被誉为“古今七律第一”
毫不为过: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杜甫《登高》
写诗如此,
已经无法品评——
任何注脚和赏析实属多余。
登临之悲、之愁、之苦,
至此被老杜划上了一记无比有力的句点。
写登高之诗的人再想超越,
已宣告不可能,
除非换个心情和视角。
聪明人总是不缺的,
比如宋人黄山谷:
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
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
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
——黄庭坚《登快阁》
登临高处的黄山谷,
没有想太多,
或者没有去写太多心中所想。
他好像只立意要做一件事:
鸥鹭忘机,快意平生。
他可能联想起他的良师益友苏轼,
那个写就《超然台记》的苏轼,
“吾安往而不乐”
——的确,
仕途的坎坷算不了什么,
古今的兴衰也与我无关,
人生的苦短又何必去理会!
说什么“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说什么“登高迎送远,春恨并依依”,
我只看到“天远大”、“月分明”。
人当“游于物外”,
登高还是临川,
在此抑或在彼,
哪个不是我呢!
在这样的登临诗面前,
人们暂时记不得愁苦的老杜了。
这是宋人的淡然。
淡然到即便起了忧思,
嘴里说道心惊,
文字却波澜不起。
于是,
超然淡然,
形成一份优雅,
这就成为宋人的胸襟和怀抱。
高楼聊引望,杳杳一川平。
远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
荒村生断霭,深树语流莺。
旧业遥清渭,沉思忽自惊。
——寇准《春日登楼怀归》
寇准在春日里登高怀乡,
笔调也是同样的安静恬淡。
颔联颈联都明显在仿唐朝诗人韦应物,
但整诗的调子却更倾向于王摩诘。
相对于其他伟大的前辈诗人来说,
宁静的王维明显更符合
宋人的审美趣味。
登高,
不仅可以思古怀远、抒发胸襟和怀抱,
也可用以寄托对远方亲友的思念之情。
王维那首有关重阳的诗家喻户晓: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王维的登高诗,
没有李白张扬个性的豪情壮志,
没有杜甫痛思家国的沉郁悲凉,
没有崔颢遥想仙踪的不胜怅惘,
没有王勃物是人非的黯然神伤。
他想家,想亲人,
仅此而已。
所谓“高处不胜寒”的隐喻,
在此并不存在。
于是,“高处”和“低处”之差异,
在王维诗里亦无分别,
空间的分别既然没有,
时间的分别亦复如是。

沐斋作品《风月 山谷》
雪带烟云冷不开,
相思无复上高台。
江山况是数千里,
只听嘉声动地来。
——雪窦重显《寄乌龙长老》
这是有宋高僧雪窦禅师的诗作。
雪窦在一个寒冷的冬日,
思念他的朋友乌龙老和尚。
怎奈飞雪飘零,
不能够登高遥望以寄相思,
所幸乌龙和尚禅风广布,
千里传音,
也算对老友来说最大的安慰吧。
王维和雪窦的诗都可谓浑然天成,
韵味是如此的平淡,
简直看不到悲,
也读不出愁,
但深切的意味恰在其中。
就像这爿不显眼的禅门公案:
曰:“步步登高时如何?”
师曰:“云生足下。”
(《五灯会元》卷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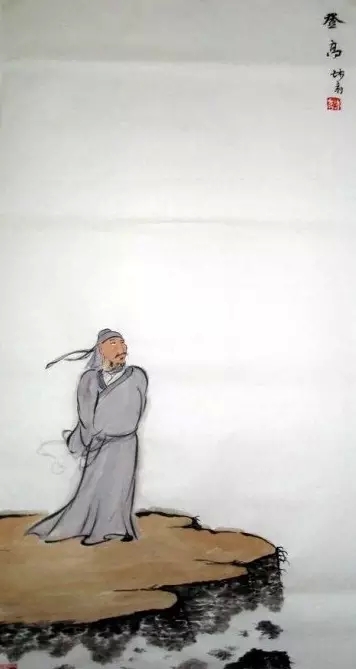
沐斋作品《登高》
石霜楚圆禅师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回答,
实则已过万水千山。
这份轻描淡写,
是禅师的胸襟。
山是静的,云是动的,
但不论动静,
都随我的脚步而存在
——禅心在此。
千年前,
那位叫范仲淹的老者登上岳阳楼,
挥毫写下自己的理想,
这个理想也是他人生的总结: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便是“志在高山”,
也便是“云生足下”。
此文章已经得到作者授权,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