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近年来,学科分支细化诱发的学术视野萎缩,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中逐渐显现出的弊端。在传统人文学科中,我们日益怀念渐次远去的“通儒”,他们宏阔的学术格局和丰盈的精神世界,都成为这个时代的奢侈品。
“通儒”对传统学术的继往开来,究竟有怎样的意义?如何在现代学科体系中,让老一辈“通儒”发挥作用,让新一代“通儒”逐渐养成?是王宁老师在这篇《打破学科壁垒 培养通儒人才》中讨论的主要问题。我们推送此文,以期引发更多对此话题的关注和思考。
打破学科壁垒 培养通儒人才
作者:王宁
近现代学术的发展往往以一些新学科的自我定位为重要标志,而定位的结果就是学科愈分愈细;然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那些世界级或国宝级的专家,却往往是跨越几个不同学科的通儒。
近几十年来学科结构的细化,导致了学术人才培养中“画地为牢”的倾向,一方面,旧时代培养起来的少数通儒在人材培养上受到极大的限制,另一方面,学术新人的知识面越来越窄。结果就是,学术愈发展而通儒愈少。
原有的通儒其才未尽其用,新的通儒培养不出来,学科就会慢慢走向萎缩,又怎能有持续性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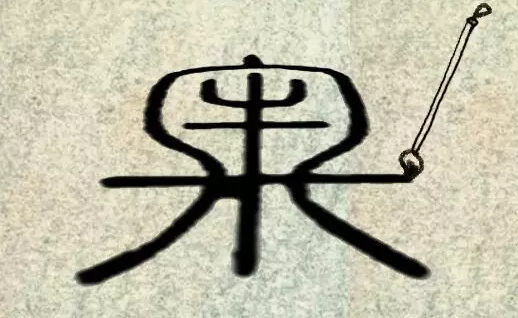
从学科上说,高等学府的文科是累积型的学科,学术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要依靠材料、观点和理论知识的积累。它与自然科学中那些必须不断进行理论和规则更替的应用型学科不同。文科特别是其中的传统学科,想要出最佳成果,超过前人,必须有所“厚积”。“厚积”非一时一人可以完成,所以要特别重视师承。
老一辈人文学科学者在受教育时,并不遵循现在规定的学科结构,他们的知识和经验都不以现有的学科体系划界;他们丰富的人生、社会体验,使本来积累的知识炉火纯青,这岂是某些学科所能框住的?
一位国宝级的专家的宝贵之处,就在于其精外有博、博中有精的独特风格和不同一般的学术内涵。然而不幸的是,半个世纪人为划分出来的学科,再挂上一个不许超越的“教研室”牌子,把一些老专家放到里面,只能让他们大材小用、大智变愚。
以启功先生为例。启先生的出身、早年经历和自己的好学深思,造就了他睿智的学术眼光。青年时代得遇陈垣校长和其他几位名师,又推动他学识的精进。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独到的体验比比皆是,他对字画碑帖的鉴定,对传统诗词书画的美学价值和内在规律的探讨,对汉语汉字的理解,都可以说是“身怀绝技”。尤其是他在表达上富有个性的言语方式,可以称得上“唯一”。
他的学养带有综合性,带有经验性,一旦把这些价值限制在学科的小格子里——比如古典文学,文献学,书法学等等,原有的知识内涵就无法充分体现了,反而不如那些一开始就在小格子里培养出来的人那么适应。
当年,启先生的博士点儿曾挂过“黄牌儿”,为这个我去找过当时的学位办,他们说:“启先生字写得好是不假,可他老人家的博士点是‘文献学’呀!”要不是高校古委会安平秋教授出手搭救,那博士点恐怕早就被“灭”了。听完那个答复,我才明白启功先生为什么最讨厌人家称他“书法家”,当初要他牵头创建“书法博士点”,他坚决拒绝。用启先生的话说:“写字能培养什么博士?”
启先生也不是很喜欢“文献学”这个名称,多次对我引用《尚书大传》的话说:“‘献,贤也,万国众贤共为帝臣。帝举是而用之,使陈布其言。’文是写下来的,献是说出来的。古代、今天的历史、理论都是这么传下来、传出去的。文献学岂不是管着所有的学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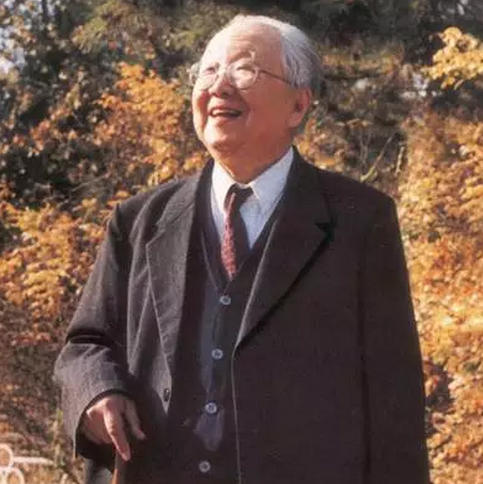
启功先生
2003年,北师大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成立的时候,三个“学科”综合,当时的理念是:钟敬文先生的民俗学是底层文化,启功先生的文献学是上层文化,我的老师陆宗达先生的传统“小学”是基础工具。三者结合起来,才能拓宽研究。
当我向启先生说明这个意思时,启先生用他特有的表达风格说:“钟先生、陆先生两家,一个是口头,相当于“献”,“献”中的“黎献”就是民俗;一个是“文字”,当然是“文”;两者岂不是都包含到“文献”上了。钟先生、陆先生都是我敬重的长者,他们各自的学问都是我拜服的,全让文献收走了,折煞文献也!”研究中心定名时,启先生坚决不用“文献”为名,之后改成“典籍”,他才默许。
我也常常想起自己的老师,陆宗达先生在20-40年代讲过的课,除了文字、音韵、训诂,以外,还开设过汉魏六朝诗、《文心雕龙》等文学课,他跟黄季刚先生多年,这些课的根柢是错不了的。可是50年代一划学科,他也只能跟俞敏先生一起去讲现代汉语语法。
学科划细,藩篱重重跨不过去,学科壁垒把人套住,怎能人尽其才?这不仅关系到老专家,也关系到青年学者的成材,关系到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在人为画定的小框里,老专家难以施展身手,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培养出来的人才知识趋窄,眼光趋短。换言之,跨学科、知识面广博的“通儒”难以造就,人为划定的学科单打独斗,发展、应用都受到局限,其实正处在隐性的萎缩之中。
学科分类越来越精细,学科关系越来越单线,美其名曰“术业有专攻”。你专攻这一点,我专攻那一点,你不许我进来,我当然也不敢进去。大家都守着那一亩三分地,种着那一样承包的庄稼,地越种越薄,增产的希望从哪里来?
我初回北师大那些年,遇到两件事。第一件,启功先生写了一本《汉语现象论丛》,在我看来,他对汉语特点的领悟实在敏锐,他送给我们教研室一位先生向他请教,有一次在路上遇到这位先生,很恭敬地问这本书他看了没有。不料这位先生到了教研室会上,跟大伙说:“看见没有?外行人都来讨论咱们的问题了,咱们也得赶快写东西了。”这一个“外行人”和一个“咱们的问题”,可不是应了我的那句“你不许我进来”的话!
另一件是我的一位师妹邹晓丽写了一本讲《红楼梦》的书,叫《试解其中味》,专门分析《红楼梦》里人名、地名的谐音双关,见解独到,我看得津津有味,劝她开一门“《红楼梦》研究”的选修课。可她说:“这是人家教研室的课,咱们去开不是得罪人吗?”这一个“人家”和一个“得罪人”,可不是又应了我那句“我当然也不敢进去”的话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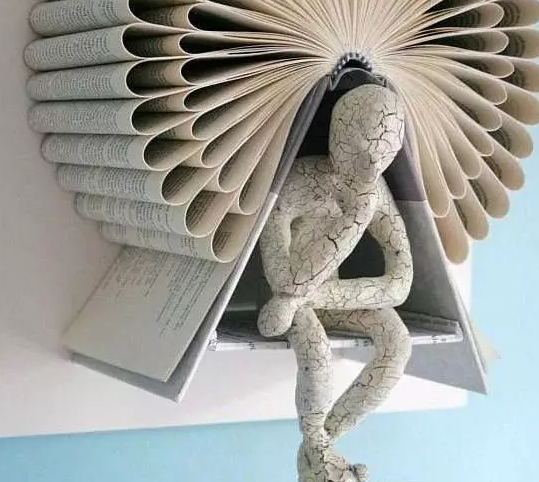
打破学科壁垒
学科壁垒森严,似乎是中国特色。北大的牛大勇老师对哈佛的历史学科作了一个调查,他说:“哈佛大学的历史教学任务,不是以一个系承担,而是以历史学系为主,由考古学系、人类学系、古典学系、东亚学系、历史与文学系,以及政府学系、法学院、经济学院等等共同承担,每个本科生要求必须上的专业课和与专业有关的课程,不及开出的全部课程的一半。”
前人的经验也可借鉴。清代的大学者戴震,精通天文、地理、哲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可称通儒,而他的几个弟子则各继承发扬其中一门学科。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其学问涵盖经学、历史、哲学、文学、中医、“小学”等领域,他的几位弟子也基本是在其中一方面深造有独得……尽管就他们两辈师生而言,学术传授没有受狭小学科结构的限制。可是说起来,也只有戴震和章太炎这样的学者,可以叫通儒。
其实,科学的学科结构稍细。就现代科学而言,倒也不妨。但高校的课程结构必须多学科贯通,尤其是传统的人文社会学科,按现代学科结构划分的现行教研室格局必须打破,只有这样,堪称通儒的大家,自己才不会受委屈,育人的作用才能得到全面发挥。
清·戴震像
(2015年7月后记:这篇文章2000年发表,时隔15年,又一批博学的老师陆续去世,无法弥补,也许交叉学科还可以补救万一,即使从现在开始,恐怕也要再有15年方可见些成效;而我们现在并没有开始推倒学科的壁垒,不禁让人十分担忧啊!)

王宁
1936年生,北师大文学院资深教授,北师大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中心主任,章黄之学在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