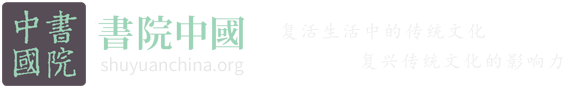【雅生活】优人神鼓:旋转在“时间之外”

【编者按】今年6月份,来自台湾的优人神鼓剧团在广州、上海、北京进行巡演。已经演出完毕的广州、上海之行给观众带来了震撼,令很多艺术专业人士惊叹不已。6月24日、25日,北京国家大剧院将迎来优人神鼓的收尾演出。敬请期待。
"优人是古老的表演者,神是自己的宁静,在自己的宁静中击鼓,就是优人神鼓。”这番定义跟随刘若r近30年。每到一处,她都会和创办人黄志群一起不厌其烦地回溯这支台湾剧团——优人神鼓的缘起。
优人神鼓的山上剧场坐落于台北市郊区,只有一条产业道路与崎岖碎石路可以联系山上与山下的世界。走到路的尽头,还得走一段山路才能到达排练场,因此也隔离了喧嚣繁杂的人世。山上的艳阳、风雨、寒流、虫鸣、鸟叫和优人的鼓声、锣声、脚步声,甚至谈笑和节拍器的声音,谱出一番幽玄的意境。他们几乎每日在山里风吹雨打,却不受外界所惑,无论心智或身体,都备受考验。
剧团以“先学静坐,再教击鼓”为原则奠定了训练及表演形式。作为一支隐居于山林、道艺合一的表演团,哪怕来到城市演出,优人神鼓的团员们依然坚持着早起练功、打坐的习惯。这种训练方式,也让优人神鼓区别于其他许多艺术团体。

1998年首部经典作品《听海之心》被法国《世界日报》评为“亚维侬艺术节最佳节目”、2000年再度被赞誉为“里昂双年舞蹈节最受观众欢迎的节目”。后又凭《金刚心》荣获2003年台湾第一届台新艺术奖表演艺术类首奖,在国际上享誉日隆,邀请不断,曾于纽约下一波艺术节和俄罗斯莫斯科第六届契诃夫国际戏剧节等演出。2015年6月份,“优人神鼓”携另一部磨砺四年的巨作《时间之外》来到广州、上海、北京的大剧院,为大陆观众带来夏夜里的禅意。
《时间之外》的出现,是机缘。刘若r描述,就好像禅坐过程,突然经历到一种无时间的感觉,能感知到过去、现在和未来。但也仿若时间不见。最开始,她想取名“无我”又觉过于宗教性,最后改为“时间之外”。通俗的解读,就如五年前黄志群在接受采访时说的——要活在当下。
当帷幕徐徐拉开,优人们定力十足的气场、沉静的气息扑面而来,让观众不由得深吸一口气,坐直了身体。《时间之外》的整场演出综合运用了多媒体投影、舞蹈、拳术、吟唱、鼓乐、筝乐等许多元素,但却毫无庞杂之感,反而给人以浑然一体、简洁凝练的印象。
舞者们身穿白色道袍,与鼓手们的黑色着装相互映衬,一黑一白令人联想到太极的意向。旋转,则是整场演出出现得最多的舞蹈动作,时而平稳如钟、时而徐疾如风,道袍在匀速飞旋中形成一个个漩涡,像钟表上的指针、天体的自转、像宇宙中的黑洞,带人漫游时间长河,穿越于作品中营造的“大骤雨”、“千江映月”、“蚀”等一幕幕亘古不变的自然现象。鼓点,有时是伴奏,有时是整齐划一的鼓舞,令人赞叹。
据说这次舞蹈的雏形,源自亚美尼亚哲学家葛吉夫在亚洲旅行时所发现的在神秘修道院里的一种古老舞蹈,也叫“神圣舞蹈”。这是一种以严格界定好的动作和路径组合而成的律动,好像太阳系诸行星的运行。优人们在舞蹈时,通过自我觉察,整合意识、情感与身体。优人们登上舞台,就犹如走上神圣而古老的祭坛。他们用自己的灵性与身体旋转出时间之外的能量,淋灌祭坛下的眼睛。

【对话 刘若r \ 黄志群】
优选择了鼓作为最重要的表演道具,请问你们如何看待“鼓”这种乐器的特性?
在我们看来,鼓确实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乐器,它的回声特别大,因此特别富有感染力。鼓,是甲骨文中第一个被解读出来的乐器,古代军队出征时,战士击打着沾满鲜血的大鼓,以振奋军心,因此有“鼓舞人心”的说法。除此以外,鼓还有安定人心的作用,寺庙里,僧侣就经常在傍晚敲鼓,我们的小女儿在澎湃的鼓声中也能安然入睡。所以,我们将鼓看成一种特殊的桥梁,可以通向人类情感最丰富的内心。
优人神鼓的表演介于音乐、舞蹈、戏剧之间,究竟应该如何定位你们的演出?它应该属于怎样的艺术门类?
优的这种表演形式,一般被称为“Performing Art”,它不同于单纯的音乐、戏剧或者舞蹈,但都属于剧场艺术的范畴。大多数现代剧场都致力于塑造角色和叙述故事,但优剧团是以击鼓的音乐和表演者动作的准确度去构建剧场的能量。我们在法国亚维侬艺术节演出时,法国《解放报》就评价说,优人即像僧侣,又像战士,既是舞者,又是运动员。优的演出就是将多种艺术形式融合在一起,要求观众不光光用耳朵聆听,更要动用眼、耳、舌、身、意各种感官来共同感受,演员的走路、旋转、鼓棰的摆动都是表演的一部分。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鼓乐,比如中国的威风锣鼓,日本的鬼太鼓座。优人神鼓与他们相比,最与众不同之处在哪里?
我们和别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训练方式。优人的“一日三打”:打坐、打鼓、打拳完全是一种独创。我们的艺术就是从这种训练模式中摸索出来的,其中很自然地融入了日常训练的内容。例如我们带领团员去“云脚”,虽然走路这种行为本身不直接在表演中体现出来,但它能够作用于演员的内心,使他们的身心获得历练,从行走中获得力量,然后再透过鼓声与观众分享和交流。我们将这种训练方式描述为“道艺合一”。
这个“道”包含了演员的情感中心、运动中心和理智中心。坊间也曾经有人想模仿优的表演,但他们能够模仿的只是乐曲旋律这些外在的部分,而演员们通过刻苦训练所悟到的“内在的道”是无法学到的。
我们也看过日本鼓乐的训练方式,例如会让鼓手去跑马拉松,以培养他们的意志力,克服内心的软弱,鼓手永远呈现出一种拼命、努力的姿态。但优完全不同,我们不要追逐,不要拼搏,而是要放下目标,恢复宁静。不论鼓声多么激烈,优人永远面目安详,就像身处台风的中心。

阿师傅以前在林怀民老师的云门舞集工作过,林老师也一直努力要从中国美学中寻找东方人的身体特点。从美学的角度看,优剧场和云门有什么不同?
现代舞的美学观完全是从西方来的,所以林老师的努力才特别有意义。而优没有西方的包袱,从一开始,我们就想从原生态的东方艺术中寻找力量。东方艺术是从内在的气韵出发,探寻与土地而非信仰的关系,所以我们会带领团员去云脚,去种地、打水,去练习太极导引。优剧场是台湾第一个在训练中使用太极导引的表演团体,也是第一个坚持在街头演出的团体,优剧团成立的第8年才进国家剧院演出。
我们独特的“道艺合一”的训练模式也是非常东方式的。中国古代传授技艺时,都是靠“口传心授”,梨园行里教徒弟唱戏,或者是教人弹琴、绘画都是用这种方式,不像西方那样先讲理论和构思,而是先让学生去做、去模仿,让他们在实践中慢慢明白。《听海之心》这个作品,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大自然当中生活,很自然就对环境有了感悟。这种训练和创作方法与西方的模式是完全相反的。
我们常看到的戏剧,往往是通过紧凑的情节和表演吸引观众。而像优人神鼓这样的,只是打鼓,完全是运用声音和舞台本身的力量去震撼观众。你怎么看待这两种形式的差别?
安静的这一种艺术不够吸引观众吗?其实鼓打起来是非常大声的,那么多人一起打鼓,融合起来,本身就已经非常震撼了。但你也要清楚,那么安静的一个内在,在打那么大声的鼓,这其实是不容易的。我们容易被很大的声音带动心里的某种冲动,这种冲动使得情感会流露于言表。但是在印度,我们发现他们在打一个很大的鼓时,非常用力,但心本身还是不动的,无论声音多么震撼,他们也不会有掏心掏肺的表情。
我在打坐多年之后,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不会再把要扮演的角色,完全当做自己的投影,这对演员来说,实在太辛苦了。这也正是我们总在说的“入戏”,很多演员演完之后还在后台哭,自己都走不出来了。但是你要知道,传统的演员在唱连坐打时,追求的是精准,不能有半点闪失。这就是一种内在的自由,他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会陷入到因为情感投入以致全程忘我。这种觉知是经过非常长的训练才能做到的。
优剧场作为一个出色的表演团体,已经走过了22年的历程,而内地的剧场艺术至今才刚刚起步。作为前辈,你们对现在致力于剧场表演的新人,有什么建言?
和台湾相比,内地有个很明显的优势,就是文化传统保留得很好,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要开拓视野,努力摸索,多花时间去走一些辛苦的路,从中获得内心的成长,发现自身的潜质所在,并且弄清艺术与娱乐的区别。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从零开始的,拿我自己(刘若r)来讲,我从大一开始学习表演,从30个人的小剧场开始,从没有一分钱薪水开始,不断寻找,不断尝试,我甚至做过从晚上十点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十点这样的“马拉松演出”。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没有任何边界的创新与突破,才能最终寻找到自己的力量所在。
(本图文根据网络内容整理而成)
上一篇:【雅生活】丰子恺漫画中的悠然茶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