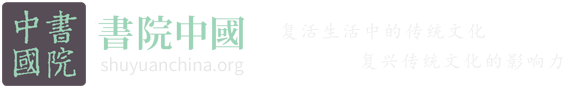【中国书院】孔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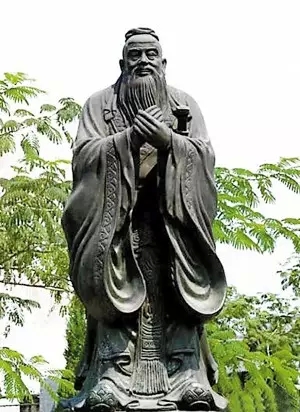
【编者按】
孔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遗传了父母的优点,身材高大,有一米九左右,在相貌上是个标准的古代大帅哥。但他出生于落魄的贵族之家,很小就没了爹,一辈子都靠自己在奋斗,一点没有“富二代”、“官二代”的运气。如果在21世纪的今天,孔子也会是一个成功伟大的人。因为他具备了成为一个成功人士的特质。他好学,他专注,他历经磨难,但依然乐观、上进,不畏权贵,保持如松柏般凛然秉直的追求。
9月28日是孔子诞辰纪念日,我们在以复古的形式组织纪念各种活动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了解真正的孔子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大家头脑中的孔子与真正的孔子到底有什么差别?为什么他的思想能够传承至今?今天,承蒙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授权,从他《永不妥协的大生命---孔子》的图书中摘取一篇文章,来还原历史上活生生的真实孔子,他既不是无所依归的丧家狗,更不是高不可攀的圣人,也不是深沉学究的书呆子,而是一位有血有肉、有脾气有性格的达人。撕掉历朝历代强加在孔子身上的政治和道德标签,我们通过李山老师的解读能看见一个满身烟火气,既乐观通透,又自由悲壮,洋溢着血性、人性和感性情怀的大生命。

孔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李山
孔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最近几年还有点小小波澜,前不久某家电视台做过一档节目,辩论孔子究竟是“丧家狗”还是“圣人”。两种说法都不是现在才有的。孔子在的时候,有人就说他是仁者、圣人,但是,孔子并不承认,《论语·述而》中,他就说过:“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圣”与“仁”的称号,我哪里当得起!我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我是不断向那个方向努力的人。所以这个你看,他不承认他是仁者,也不承认他是个圣人,他只说他也在向那个方向努力。有趣的是,“丧家狗”这个称号,他倒是认下了。
前面我们曾谈到过孔子在郑国和弟子们走散的故事,有人形容额头像谁、脖子像谁、肩膀像谁等等,孔子认为都是“末也”,不达实际,倒是对“丧家狗”的形容,孔子说:“然哉!然哉!”孔子的意思是说,别人对他的外形描述,是细枝末节,不打紧,说他是“丧家狗”,倒是很传神。孔子带着一些弟子到处周游,无所安身,可不像是丧家狗!这里,孔子幽了自己一默!
不过,孔子可以自我调侃,后人也用“丧家狗”来评定他,就难免是不知轻重和深浅了。诚然孔子一生都没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没有找到政治归宿,但这只是现实层面的失意。从精神层面看,孔子却拥有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乐观通透的精神世界。
孔子的一生坎坷,靠山山倒,靠河河干。何以这样说?孔子一辈子寻找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净遇到的齐景公、卫灵公、季桓子有流货色,晚年有个楚昭王带一点仁者的意思吧,孔子前去投奔他,还没有见到人,楚昭王就死去了!这不是让人惋惜的吗?从这个层面说,他确是像个惶惶然的丧家狗。
现在,有一个疑问应该给出回答,那就是为什么孔子周游列国却到处碰壁?为什么晚年回到鲁国仍然那样不妥协?

孔子何以处处碰壁?
一般而言,孔子到哪一个国家,一开始都欢迎他。如到卫国,卫灵公欢迎他,仪封人也想见他,连南子也要见他。可是,真正来到一个国家,坐下来,谈一谈,却始终谈不拢,即在那些所谓的贤人,也是如此。所以,孔子席不暇暖,马上就得离开另寻出路。这究竟为什么?细读《论语》,其答案,可一言以敝:就在孔子的仁的原则和精神,不能见容于当世。孔子所以到处碰壁而决不气馁,却始终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绝不妥协,也在他对“仁”的精神原则的“守死善道”。
了解一个思想家,也可以说了解世界上任何一个思想家,有一个基本的门径,什么门径?就是要顺着他的眼光去看他所面对的问题,看清楚有关于社会,关于知识,他横在心中的重要问题是什么。例如看孟子,孟子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就是战国兼并杀人太多,同时饿死人的也太多。所以他提出“制民之产”,给民众点产业,让他们活命。以孟子为例,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让孟子十分焦虑的是战国新上台统治者把国家大部分钱财都用于军费开支,整天打仗,把老百姓饿死了。所以,他要提出为民制产,提出“仁政”。
那么孔子呢?横在他心中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呢?孔子之讲“仁”,从没有讲过“仁政”,也从来不“仁、义”并称,孔子只讲仁。仁是什么?有一句话,儒家经常说,叫“仁者,人也”。听起来像废话,实则不然。翻译一下就是:他人也是人!只有把“他人”也当成你自己一样的人,才有“仁者爱人”;才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是人,别人也是人,而且是一样的人。
这我们就要细究了,谁是“他人”?爹妈是他人吗?不是。兄弟是他人吗?也不是。对父母、兄弟有孝悌之道。再往外推,邻里是他人吗?也不是他人。朋友是他人吗?朋友也不是。那么,究竟“他人”是什么人?最后的回答:是跟我不相干的人。然而儒家说,“他人”也是“人”。如此,“仁者人也”的仁道精神,考验的不是你怎么对待父母、怎么对待朋友、怎么对待乡亲、怎么对待你认识的人,而是考验的你如何对待与不相识的人,与你无关的人。
仁者人也,是一个质朴的真理,与基督教说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博爱并无二致。不同的是,西方多了一个上帝,而儒家、孔子却只是从“推己及人”开始,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东西,就不要推给别人。
不过,以上所讲,是孔子要提出一个“仁”道的本意吗?不是。孔子提出一个“仁”道,不是为所有的人立法,而是为在位者、为周贵族,为手里有权有势的君子们立法。孔子的真精神,也在这里表现得最突出。实际上,横在孔子心中的最大问题,那就是在位上的“君子”即执政者,贵族已经变得“不仁”了,也就是只顾他们自己,不把别人当人了。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礼乐,也就是西周文化,本身没有问题。“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周文化是吸收改造夏商两代文明而建构的一套文明系统,孔子是殷商后裔,可是在文化上他“从周”。周代文化没问题。有问题的是那些老贵族,他们缺少了一种基本的精神,就是“仁。”这样周文化的系统和形式虽然还在,却像一条干涸了河床,特别寒碜,破砖头、烂瓦块,柴禾棍子,惨白一片。孔子一辈子的努力,就是想在精神上给那些老贵族打一剂强心针,他想把“仁”的活水重新引入到那条干涸的河道中,使其恢复生机与活力。
这也就是孔子为什么一生不得志,到处碰壁的根本原因。孔子周游列国,他是去找那些在位者、老贵族,是想经由改造他们的道德状况,从而改善已经变得十分糟糕的社会。但是,他的作为,恰恰是与虎谋皮。试图说服老贵族行仁道,其实是白耽误工夫!他老人家周游七十二个列国,就是周游一百四十四个列国,也是白忙一场。但是,《史记》中颜渊说得好:“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见君子!”正因为列国的君主、贵族们不容孔子之道,并不表示“仁”道是错的。“不容然后见君子”,这又说到了孔子是不是“丧家狗”的话头。
这就是孔子的精神。他为了一个仁道的理想,始终坚持。不能容于天下,也在所不惜。了解这一点,一方面是把握了孔子学术的命门,同时,也可以深切理解一个非凡的人格。这也就是给康德、黑格尔写过传记的古留加说的,一个思想家,激动人心的情节就在他的思想。孔子的一生对仁道理想的追求与坚持,不因到处碰壁而气馁、灰心丧气,就是他大人格、大生命的激动人心之处。
可当他晚年穷途末路时,叶公问子路,孔子是个什么人啊?子路被问住了。孔子知道后,说,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我是个“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的人!可见,精神层面上的孔子何尝丧家?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傲慢去轻易地诋毁一个古人。孔子一生不论身处何地、有如何的境遇,他始终不忘自己人道的理想,为了这个理想他周游列国十四载,尝尽人世间的辛酸苦楚,虽然一直碰壁但从未放弃,在春秋末年那个黑漆漆的乱世,一点“仁”道的主张为苦难的人世留下了唯一一点光亮。即使不从思想的角度、单从审美的角度看,孔子的生命也是美好的。非议孔子,若是得当,是可以的,但是若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就该受到子贡那句话的奚落了:“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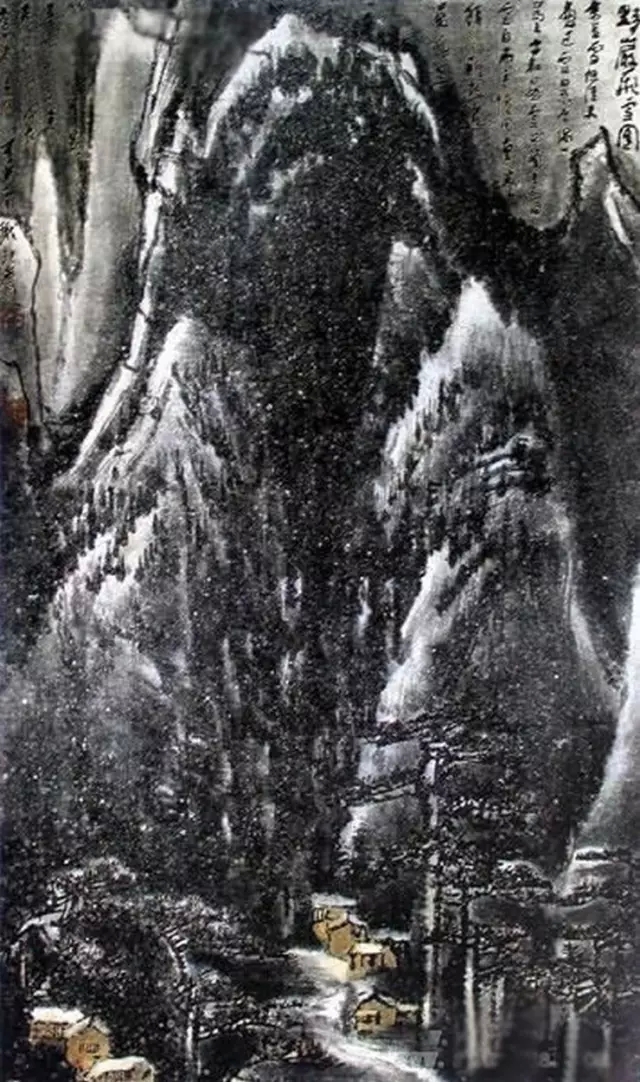
孔子的微型传记
现在有各种孔子的传记,但是最先写传的,却是孔子自己。请看《论语·为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不是一个首尾颇完整的微型传记吗!孔子自述,从十五岁开始立志学习;三十岁这年学有所成,知礼法,能独立按照礼法与人交往。四十岁时人生方向更加坚定,对自己这辈子的使命是什么不再疑惑。到五十岁的时候,知道自己沿着自己的志向前进,能做到何等地步,天生的能量到底有多大,也大致心中有数,就像爬山,虽未到端,但究竟能爬多高,远望能看到多大景观,已经大致清楚了。六十岁时听什么都觉得顺耳了,七十岁时我干什么都不会破坏规矩了。后面两句,是在说老年人的一种自由,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有一篇《论老年》,文字颇长。但孔子说老年的自由境地,简短数十个字就说清楚了。
在这篇微型传记中,十年一个境界,十年一个境界,活到七十三岁甚至更高龄的人,有的是,但顺着日子一天天的活,却难以有这样的境地攀升。孔子曾经赞美颜渊“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这句话用在他自己身上也很合适。孔子这一辈子都在奋斗。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奋进人生简短记录。这个微型传记,也可约括为三句话:少年要有功夫,中年级要有成就,老来才会有境界。
不论你是尊孔、反孔,还是批判孔,你都必须承认孔子很重要,他的人生哲学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影响了每一代中国人。就从这点说,在反孔、批孔之前,也先要老实地了解孔。孔子是个大生命,他一生奋进,一生坚持一个理想,一生都在乐观中不断攀升进取,他那种对理想的坚持和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执着,都不是凡夫俗子可以做到的。孔子的人生是一个非凡的人生,是一个有血气、有理想支撑的人生。
“圣人”、“仁者”对他的形容,太老套。
我要说,孔子是一个大生命!
【作者介绍】
李山,河北新城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启功先生弟子。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文化史、先秦两汉文学、《诗经》研究领域卓有成就,是中国《诗经》研究会常务理事。
曾出版过《诗经的文化精神》、《诗经析读》、《中国文化史》、《先秦文化史讲义》等专著多部,在《文学遗产》、《文史哲》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在学界有较大影响。
2011年李山登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春秋五霸”系列(29集)。2012年再次在“百家讲坛”主讲“战国七雄”(24讲)。曾被北师大学生票选为“十佳教师”。”还是“评师网”全国最受欢迎的“红钻教师”。
下一篇:楼宇烈:书院教育应得到体制的认同